我把自己的精神分裂症隐瞒了20年当我告诉一个朋友后,一切都变了
- 百科大全
- 2025-03-01
- 59


今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四,我和丈夫开车去我们县的警察学院训练基地。一位穿制服的军官让我们进去。我们被护送着穿过几条走廊,进入一间会议室,我被安排在那里代表我们当地的全国精神疾病联盟办公室发言。
站在房间的前面,我首先介绍了自己所有的成就——我最近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证书课程毕业,我教的课程和研讨会,还有25年的婚姻。然后我补充说:“我患有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和你们谈话的原因。”
我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关于五种类型的幻觉,我听到的声音认为自己是上帝,耶稣和圣灵,以及我如何经常因为偏执而认为我的食物有毒。我也谈到了我在精神错乱时的幻觉。
对于警官来说,听到有严重精神疾病经历的人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精神健康危机的人。我想让他们明白,精神病会让人行为不正常,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是可以成功治疗的。
我尽我所能,回答了官员们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许多人感谢我的到来,感谢我对这个诊断的脆弱性,这个诊断仍然有很多错误的信息和与之相关的耻辱。
近20年来,我对朋友、姻亲和雇主隐瞒了自己的精神疾病。自2015年以来,我一直通过讲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细节来赚取部分收入。我与执法人员、护理专业的学生、研究婚姻和家庭治疗的人以及患有类似诊断的人的治疗机构进行了交谈。
分享我的故事有助于某些群体更好地了解精神疾病,并帮助那些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在他们的旅程中感到不那么孤独。我分享的细节可以帮助专业人士更好地理解脱离现实的感觉。
在我快30岁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人们想要对付我。随着妄想症的加重,我停止了吃饭和睡觉。亲戚把我送到医院,但过了几天我才同意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我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伴有精神病特征。当时,我对成为我身份一部分的标签有很多否认和羞耻。
告诉别人我有精神疾病——尤其是和我约会的男人——几乎总是以他们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告终。我记得就在那天,一个男人说:“我真的无法处理这件事”,尽管我在他身边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我很早就知道,精神疾病会破坏很多关系。
当我遇到我现在的丈夫时,他也对我的诊断持保留意见。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不遵守我的药物治疗,所以我在严重的发作中进进出出。我曾两次试图自杀,并多次出现幻听、妄想症和妄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团结在一起,即使在他看到我的症状后,他还是继续支持我。在我们在一起不久之后,我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我的治疗,我们能够集中精力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婚姻奠定基础。
到那时,我已经学会了不向别人提起我的病,所以这成了我和丈夫之间的秘密。我的家人知道,但我们没有告诉我丈夫的家人。我们没有告诉他的任何同事,也没有告诉我们在洛杉矶市区附近买了一套公寓后结识的朋友。
不仅仅是我所经历的耻辱和拒绝让我对自己的挣扎保持沉默。这也是社会提供给我的关于我的病情和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的信息的内化。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可爱,不那么讨人喜欢,知道的人会认为我“疯了”。
我有一段稳定的时期,持续了将近10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全职工作,上课,并担任市议会委员会的委员。我有一起工作、一起远足、一起打壁球的朋友,我和丈夫也经常去海外旅行。
我的精神科医生认为我的诊断有问题,并让我停止了所有的药物治疗。一年之内,我24小时都在幻觉中,不睡觉,完全脱离了现实。在医生再次稳定我之前,我的精神状态持续了六个月。
这些新医生诊断我患有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对我和我丈夫来说就像一记重拳。我得知消息的那天,我们几乎没说过话。我记得我丈夫最后说:“好吧,你今天和昨天没什么不同。”这番话让我确信,即使有了这个新消息,他也不会去任何地方。
然而,我们加倍保守这个秘密,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我的病情更加保密。我想象如果人们在我告诉他们我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时拒绝我,那么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患有精神分裂症,情况会更糟。
这个新秘密在我们和家人之间保守了将近10年,直到我的精神科医生给我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让我告诉我的一个朋友我的诊断结果。我的精神科医生意识到,如果我对影响我生活的事情保守秘密,它会阻碍我与他人真正亲近。她知道躲藏会把我和别人隔离开来。
我丈夫和我讨论了几个星期。在秘密地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反复考虑是否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病情。我们谈到了失去朋友。我们谈到,一旦我们告诉了一个朋友,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最后决定告诉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密切合作的一位社工。
吃早午餐时,我的声音颤抖着说:“我有精神分裂症。”起初,他有点吃惊,问了一些问题,但谈话并没有占据我们早午餐约会的时间。那天晚上,我为一家在线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我精神疾病经历的文章。文章发表后,我在Facebook上发布了它的链接——我的公婆、同事,甚至从高中就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患有精神疾病。
我们失去了几个朋友。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像那些早期的男朋友一样认为“我处理不了”,或者他们是否因为我们对他们隐瞒了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感到不安。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人知道他们和我们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亲密,是因为我们没有过一种真实、完全开放的生活,这是否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我觉得自己很脆弱,害怕最终说出我的秘密,但也有一种巨大的解脱。自从我30岁出头以来,我第一次可以谈论自己,而不用隐藏我的大部分现实和我是谁。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写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讲述我的故事让我在NAMI得到了一个职位,让我站在几十名警察面前,解释处于精神健康危机中的感觉。
我的秘密已经成为我的工具,我不再隐藏它。每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或者每当心理健康成为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谈论它。我觉得我在利用一个困难的情况来改变别人的生活,这让我的精神分裂症经历变得有意义,并把它变成了不完全消极的东西。
与那些支离破碎、与亲朋好友失去真正亲密关系的岁月相比,我在2023年遇到的耻辱少了,好奇心也多了。我大胆地做我自己——我真实的自己——我正在用这个曾经紧紧保守的秘密,希望能让像我这样的人不那么难以面对精神疾病的现实。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需要帮助,打电话或发短信988或聊天988lifeline.org寻求心理健康支持。此外,你可以在dontcallthepolice.com上找到当地的心理健康和危机资源。在美国以外,请访问国际网站美国预防自杀协会。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需要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一份建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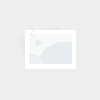






有话要说...